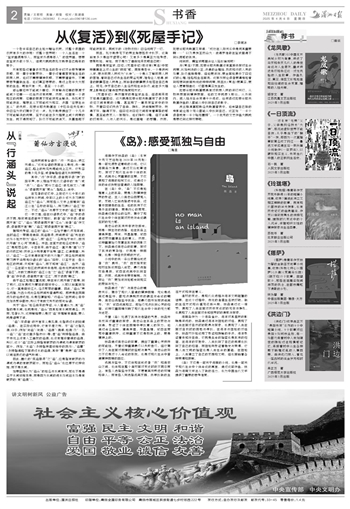□李婉冰
一个老爷将自己的土地分赠给农民,对整个俄国的农民有多大的作用?对整个世界呢?一个人生活在一个“监狱里满是好人,而监狱外满是恶人”的世界里,想要在监狱外做个好人,结局大概就像托尔斯泰自己晚年的样子。
只有那些过着奢侈放荡生活的老爷们才会思考精神救赎。而一辈子辛勤劳动、一辈子过着痛苦艰难生活的底层人民,他们不需要精神救赎,不需要福音书,不需要思考重新生活。他们真正想要的,是过上老爷太太那样的生活,哪怕只有一天,甚至一个小时。
惩治罪犯并不能减少罪犯,只有解决犯罪的根源才能减少犯罪——这当然没有问题。然而,这里有一个很现实的问题:犯罪的根源不可能被完全解决。乌托邦不可能存在,理想主义不可能成为现实。法国“空想社会主义”的失败,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卡拉马佐夫兄弟》中已经为我们揭示了这一点。托尔斯泰提出了一个几乎不可能解决的问题,至于这能在多大程度上减少问题的发生,就不得而知了。阶级不可能被消灭,贫富差距不可能被抹平,奥威尔的《动物农场》已经说明了一切。
而且,托尔斯泰笔下的男主角想拯救卡秋莎,这背后有多少是出于虚荣心呢?又有多少是真正为她考虑,想帮助她、爱她,而不是为了借由她来救赎自己呢?
同样是写监狱、囚犯,《死屋手记》却没有《复活》中那种高高在上对众生的“俯视”感。同样是老爷,一个是被判入狱,想与底层人民成为“伙伴”;一个是从了解底层人民的苦难,看到自己过去生活的荒淫无度,难免让人觉得,前者的眼睛落在人民身上,而后者的眼睛更多地落在自己身上。可见,作家自己的人生经历和社会阶级,能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他们看待世界的角度和方式。
《死屋手记》虽然描写的是监狱生活,但读起来却不觉得沉重苦闷。这大概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写了很多苦役犯之间有趣的斗嘴,甚至用了一章来写监狱中的动物。尽管囚犯们失去了自由、隐私,被迫强制劳动,吃得不好,睡得不好,但囚犯与囚犯之间却有着真挚的感情,甚至能像家人一样相处。他们争吵斗嘴,但不会真的打起来。人与人的关系,是这里唯一的慰藉。然而,陀思妥耶夫斯基又写道:“成功在人际关系中是何其重要啊……”以及贵族亚历山大·彼得罗维奇在监狱里得不到认同感的孤独。
说到底,蹲监狱哪里会让人轻松愉悦呢?
与《复活》不同,陀思妥耶夫斯基没有直接去探讨社会问题,比如判决的公正、法律的合理性、执政和行政人员的处事、阶级差异等等。但他更深刻、更全面地展示了囚犯们的心理、性格和生活面貌。这样反而让读者更清楚地看到和想到前面所说的种种问题,而且比《复活》更真实,更让人愿意相信这一切都是真实发生的。
陀思妥耶夫斯基更具有对底层人民的深切关切,从物质层面到精神层面。他的文字就像X射线,从外到内,把人性与社会写得十分透彻。任何读过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的人都能从中找到自己的影子。
波兰导演基耶斯洛夫斯基曾表示,他希望自己拍的电影能让每个观众都能从中找到自己。这正如“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一个优秀的文艺作品大概就是要达到这种效果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