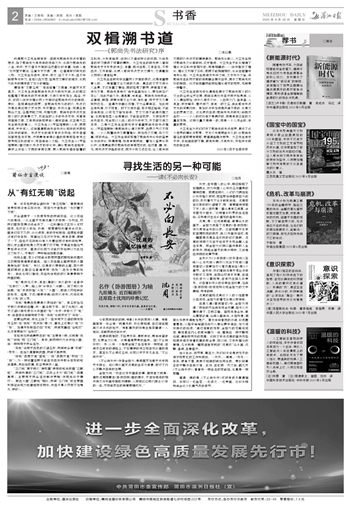□朱以撒
听闻郭大卫先生早有写一部研究郭尚先书法专著的想法,除了郭尚先为其宗亲的缘由之外,也因为郭尚先的人生、学识、艺文诸多方面的经历都比较丰富,如前人言“功烈显于朝廷,名誉光于竹帛”,是一位值得探讨研究的人物。大卫先生好读书、写字、写文,出了不少书,且不中断思考与学习,自觉以古为范,坚持艺文兼修的追求,也就为此书的撰写做了充分的铺垫。
莆田有“文献名邦”“海滨邹鲁”之美誉,书画艺术家甚多。大卫先生选择郭尚先书法为研究方向,比较翔实地整理了郭尚先的家学渊源、交游及学书观念、路径、方法,试图从创作与理论两个方面印证郭尚先成功的原因,寻找一些规律性的因素。在郭尚先所处的时代,书法仍然是日常运用之艺与技,书家辈出、书风纷呈,可谓各抱荆山之玉,各握灵蛇之珠,风雅无限。郭尚先的书法放在那个时代的背景之下,放在当时众多的书法家中,究竟有何差异之美,又有何创新可使后人得到启迪,这正是大卫先生研究的意义。大卫先生从《芳坚馆题跋》入手,层层递进,步步深入,逐渐厘清郭尚先在书法认知中的关捩和实践中的辙轨。书法艺术的追求有许多共性,学书者循旧辙而自足怀抱,然而最有审美价值的却是那些有独立思考和实践的部分,可启迪后人之路。大卫先生从《芳坚馆题跋》里对前代书法家的评论中,确认郭尚先在帖学、碑学上与他人不同的审美态度,更从郭尚先诸体皆擅的实践中,分析其临写、创作以及诸体转化的成因,为后来者的学习提供了可靠的襄助。大卫先生的研究使人看到郭尚先艺术形象的独立、丰富,既与古契,又有自见;不乖古法,又开新辙;也使人感到书法艺术之博大,勿谓雕虫小技可以漫言轻易。
大卫先生在研究中注重两个方面的表达,这是有重要意义的。一是看重文士之间的交游。真正的文艺交游令人生慕,不仅丰富了情性,同时拓宽了眼界,使群居不倚,独处不惧。郭尚先有诗云“尚书鉴画如论人,要见铁石广平心”,如此方能久长,得其真,受其益。郭尚先与林则徐、梁章钜、顾莼、伊秉绶等文士交游,有私谊,而于艺文之事则抒己见,一室清欢中剧谈风雅,不为尘事牵率。如此则各有所得,妙不可言。时下交游亦盛,却多相互蹈袭,不能自适其性,以致笔下皆如伯仲。艺文交游不能得风雅之旨,也就难免落入俗常窠臼,不能自出机杼。交游如何不迷失自我,完全可以从古人的行为中学习,方不蔽交游之本来。二是大卫先生在研究中亦看重郭尚先的书法理论。《芳坚馆题跋》是郭尚先心得之积累,古穆之气终不可磨。一个人既擅创作又兼擅理论,则如舟之双楫、鸟之双翼,可致远矣。大卫先生细致梳理了郭尚先书论中的鉴赏论与创作论,揆情度理,析其审美倾向。譬如从鉴赏论来认识,这是最能表达郭尚先的审美范式的,他对晋、唐、宋、元、明书法家作品的评述,既予分析又述己见,让人感受到不同时代书法家的精神律动。郭尚先论前人,大卫先生则对郭尚先之论再研判,逐步推进。大卫先生于此也强调了理论与实践并非相斥的,而是相融的——创作推动了理论,理论又引导了实践,即便不能相辅相成,也会在碰撞中有所认知。大卫先生既追求书中之味,又求书外之旨,将郭尚先在此两方面的细微融合揭示出来,展示了郭尚先成功的原因。这对后世重技能而轻理论追求的现象,无疑是一种警示。
大卫先生在研究中也清楚地展示了郭尚先那个时代文士的治学治艺态度,即由日常功夫自然而然地浸润,从个人情性而始,作长久追求之计。入古贤之门,登其堂、入其室,积岁解牛,砉然游刃,非徇一时之名,由此感受书法艺术的深厚内质。身加修与学加进是共通不悖的,也是文士的素常之态。这也使我在读《郭尚先书法研究》后慨然生叹——一个人的成功绝不是偶然的,而是有很实在的力量在支持。这种力量不是单一的,而是一个人综合的、丰富的素养。
大卫先生为我们打开了郭尚先的书法世界,展示了这个世界的精彩与繁复。艺术终究是更能长久的,比郭尚先曾经的官职更有美感,更值得品咂与思考。大卫先生有志于学,日后宜砥砺不懈,箴其所阙,济其所长,开拓学术研究的新空间。
2025年2月于古邑怀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