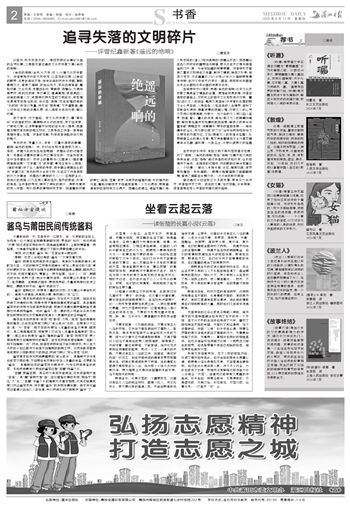□陈锦
大暑前后的一天,笔者走访一位朋友。在一处房前的空地上,发现有一位大婶正在用簸箕晾晒东西,素色的“饭巾”(传统民间“炊粿”和过滤豆浆用的布巾)四角垂在簸箕外,上面则覆盖着一层稻草。大婶拿开稻草后,露出了下面长满黄色霉丝的米饭。
“婶阿,你这是做‘酱乌’吗?”笔者饶有兴趣地问。
“是啊!你怎么会知这是做‘酱乌’?”大婶笑着反问。
“酱乌”就是本地民间的传统酱料。其原料为新鲜的糙米(或酌加大豆),大致的制作工序是先把糙米(或加入浸泡过的大豆)煮成较硬的干饭,再把干饭摊开在簸箕等晾晒器具上曝晒,晒到两三成干后,收回放置室内,覆盖上一层干稻草。经这么一“闷”,晾晒过的米饭(或熟大豆)就会长霉并结块。待到霉丝长得差不多长了,继续曝晒。在晾晒过程中,要把块弄碎,尽量保持原料的独立颗粒。曝晒足够干后,“酱乌”就做成了。
“酱乌”呈颗粒状,并带有少量的粉状物(多为霉丝干燥后形成的)。通常为深褐色,质黑而泛黄,是民间以“乌”名之。
“酱乌”是本地民间的传统酱料,犹如北方之豆豉。但在本地民间不作调味料用,而是专用于腌制超高咸度的酱菜。其在腌制酱菜中的作用犹如做酒使用的曲,即通过缓慢发酵使腌制品变得糜烂并具特殊酱味。说到“酱乌”,老一辈的老乡可能会条件反射般地联想到传统农家腌制的咸得令人皱眉咋舌的各种酱菜。
腌菜在本地民间有“咸菜”和“酸菜”之别,“咸菜”指的是高咸度的腌菜,这类菜在民间习惯以“咸头咸渗”统称。主要有以下三类:其一为“菜咸”(用芥菜的叶梗加入足量的食盐反复煮、晒而成);其二是鲜腌咸菜(用鲜萝卜切条加入足量食盐腌制的“菜头青”);第三类也就是加“酱乌”腌制的酱菜。“酸菜”则用芥菜、萝卜等适度脱水后腌制而成的腌菜。在本地民间有湿性腌制(“压酸”)和干性腌制(“纳”)两类,前者可供即食但不能长期存放,所以在大多数的小地区都作为后者干性腌制的前期工序。这两类酸菜都具有咸度较小而酸度较大的特征,民间习惯以“菜头菜尾”统称。
酱菜是本地传统民间最重要的“咸头咸渗”。其腌制方法与其他咸菜不同的是,不但要在食材原料中加入足量的食盐,还要酌加“酱乌”。其腌制出来的酱菜可长期存放,为传统民间常备的咸菜。本地民间最有代表性的酱菜应推“豆髓”和酱冬瓜。
“豆髓”即酱豆腐。其名称为连读变音词组,逐字读音同方言“豆祖”。其“髓”音同方言“祖”,在这里指浓稠的东西,相当于“腐乳”之“乳”。“豆髓”与酱冬瓜的腌制方法基本相同,均凭仗超高咸度以防止酱菜变质,并依靠“酱乌”的作用缓慢发酵。由于传统酱菜已普遍淡出当代人的饭桌,所以民间也就不再制作“酱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