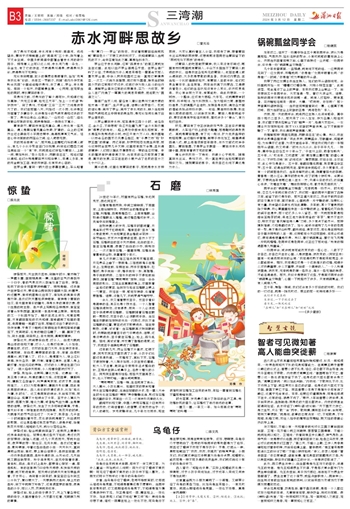郑倩 作
□林秀莲
20世纪70年代,村里有两台石磨,东边阿秀家,西边阿玉家。
石磨有磨扇两块,中间立轴链接,下扇固定,上扇绕轴转动。两块咬合的磨扇留有一个空膛,叫磨膛,四周是磨齿纹。上扇有磨眼,谷物通过磨眼流入磨膛,通过磨齿磨成粉末,从夹缝中流到磨盘上。
在物质匮乏的岁月,石磨平时都闲置,只是逢年过节才忙碌起来。磨蚕豆做“豆冻”,磨小麦做麦煎,大米和黄豆混合磨做浮菜饼……年节临近,家家户户都要做豆腐,自然少不了石磨,石磨研出的豆汁天然美味,乳白的豆汁,挂在石磨周围,像围了白白的纱巾,特别动人。一次次推动石磨,一圈圈旋舞,石磨流淌着喜爱的谷物,丰富着那个年代。
有几次我跟二姐三姐去阿秀家磨豆腐。只见悬梁上垂下一根麻绳,二姐把麻绳系在磨手上,左脚在前,右脚在后,两手紧握磨手,拉磨时,身子向后一仰,磨手向右一折,再推磨,身子向前倾俯。二姐长长的辫子不停地前后摆动,随着石磨“嘎吱嘎吱”旋转,划出一条条美丽的弧线。三姐坐在高高的凳上,怀里抱着一盆泡过的黄豆,恰到好处地往石磨眼上喂上一勺黄豆。我站在一旁,感觉好神奇,也缠着要推磨。结果,没推几下,我就累得气喘吁吁。
一会儿,我又缠着要放豆子。放豆子看似是简单的活,其实也是个技术活。一个人推着石磨快速转动,没有停息,而另一个人必须把豆子快速喂进石磨眼。石磨眼随着石磨在眼前一晃而过,放豆子的人必须眼疾手快。当石磨在我眼前如旋转的木马一闪而过,我找不准石磨眼的位置,黄豆迟迟不敢喂进去。姐在旁鼓励,没事,试试看!当石磨眼再次转到眼前时,我果断把装着豆子的勺子喂进去,结果,还是没喂进去,豆子撒在石磨上、地上,四处乱跳。姐说,再试试看,并放慢了推磨的速度,这下,我把豆子准确地喂进了石磨眼。
过年前几天,两台石磨不分昼夜,忙碌不停,阿秀家阿玉家都挤满了乡亲,小孩子们也都过来凑热闹。一家磨完了,再轮下家,石磨不停旋转着,大人挥汗如雨,小孩在旁边嬉闹,趁大人不注意,跑到盆子旁用手沾点雪白的粉,互相点在额头或鼻子上,活像个唱戏的小丑。阿秀阿玉都是好性格,那些天家里再怎么吵,也从不唠叨啥,一副乐呵呵模样。
“嘎吱嘎吱”,石磨一响,生活就有了奔头,大人高兴,小孩也高兴。地里收获的粮食和着井水在石磨中碾碎,流淌出甘甜的汁液,老一辈人大半生时光也在石磨的“嘎吱”声中静静流淌,熬过如石磨般沉重的日子,养育出一代又一代有质朴风骨的儿女。
翻阅材料和文献,中国人使用石磨至少已有两千年的历史,它凝结着前人的智慧,还有历史给予一代代人的寄托。岁月寂静深流,几十年匆匆而去,现在很难吃到石磨加工出来的食物,年轻一辈看到石磨也不懂那是啥东西。
时光荏苒,岁月最终淘汰了陈旧的生产工具,电动磨粉机的普及,让石磨成了渐行渐远的往事。
一圈又一圈,一年又一年。如今却再没有“嘎吱嘎吱”的吟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