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清华
小时候,父亲身体健硕,性情开朗,颇多才艺。生产队出工回来或下雨没出工的时候,我们几个兄弟姐妹常常围坐在父亲跟前,父亲就拿出他的当家宝贝——二胡、笛子,开始忘情地演奏。一曲曲悠扬的曲子,从我家简陋的瓦屋飘出,飘荡在乡间明净的天空。有时,他会随二胡的曲子唱起那时的流行歌曲,我们便也歪歪扭扭地跟着父亲唱起来:“花篮里花儿香,听我来唱一唱……”有时暴雨初歇,父亲就从楼梯拐角的角落拿出罾子或大网,叫我背上鱼篓,去池塘河沟里抓鱼。抓到鳗鱼时,我常常不敢下手,父亲对准鱼鳃处一掐,就抓住了,我把鱼篓的口凑过去,鳗鱼就溜进了鱼篓。父亲写得一手好字,是生产队的记工员,每天晚上要把生产队出工的情况登记下来。有时他也会教我二胡和笛子,教我写字,教我唱歌。父亲还是家族里的说话人,大事小事都能说上一些令人信服的道理。
那时候,父亲的脸上笑容洋溢,我常常看到幸福从他的眼中出发,前往他周围的世界,有时也会到达我的心里。
渐渐长大了,我对外面的世界充满好奇,一天天都在想着走到更远的地方,去看看不一样的世界。那时,改革政策已出,田地承包到户。父亲依然身强体壮,忙完自家田活,还自腌咸菜卖。父亲越来越忙,家里的二胡声笛子和歌声也越来越少,直到有一天,父亲发现挂在墙上沾满灰尘的二胡已经断了一根弦,于是,家里再也没有了二胡的声音。
一天,父亲骑车经黄石去涵江调查咸菜市场,我便跟着父亲去瞎逛。一路上,自行车疾行如风,坐在自行车后面,我心情愉悦,欣赏着眼前闪过的一幅幅水乡画卷:小桥呵护着流水,绿树守望着水田,水田里插秧的老农,水田上掠过的燕子,水田旁瓦房参差的村落,村落中沧桑的祠堂,祠堂边苍老的榕树,榕树下寂寞的石桌,古老的宁海桥,奔腾的木兰溪,梅妃出生地,戚公抗倭处……
正当我目不暇接的时候,忽然眼前一亮,一片清灵的湖水在繁花茂叶之后,向我展开了洁净的肌肤,微微涟漪在春风中温柔地漾开,把倒映湖面的树影人影云影和房子的倒影,一一摇化。我心中一酥,倏然醉了。想不到会有这样一片清滢的湖水,安详、静寂地偎依在我生命历程的某一个角落,等待着有一天和我相遇。
我问父亲这是什么地方,父亲说:“白塘。”
更让人惊艳的是湖边的梅花。满树满树的梅花,开得灿烂、热烈,引得蜂蝶成群,游人如织。
父亲也被梅花吸引了,就停下自行车,带着我走进梅园。梅园不大,但每一棵树上都缀满花朵,色彩艳丽,近根部的花开得早,多已枯萎;中间部分的正在尽情绽放,朵朵饱满,摇曳多姿;枝末的许多花蕾,仿佛在酝酿力量,等待最合适的开放时机。
父亲默默看着梅花,而我却发现,父亲的鬓角,开始冒出几根白发。
大一寒假回到家,发现父亲病了。父亲整个胃都切除了,瘦得皮包骨头。我心疼不已,又不敢多问,心里有一股难言的烦闷。那次去涵江医院拿复查的报告单,忽然想起父亲曾经带我到过的白塘,就顺路去走走。其时北风时起,冬阳清冷,白塘湖面波光粼粼,几只白鹭掠过,轻盈地划着优美的弧线,阳光下,它们白色的身影优美得有点虚幻。
来到湖边的梅园,我发现那片玉树琼枝还在阳光下安然默立,仿佛等待着某一个庄严时刻的来临。几个俏皮的花苞正欲鼓蕾而出,几片嫩绿的叶芽也在探头张望,而几只勤劳的蜜蜂发现一无所获后,在树林上绕了几圈,悻悻离去。
我坐在湖边的石椅上,静静地看着湖面,想平复一下心情。忽然,湖边向阳的地方一朵早开的梅花引起了我的注意。它孤零零地独立枝头,看着倒映水中的影子,仿佛听得见它微微叹息的声音。只有阵阵微风拂过,它才勉强打起精神,轻轻抖动了一下。
看着它孤芳自赏,郁郁寡欢的样子,我只觉得那一刻,周围的世界全都淡去,只剩下它和我,站在一个孤独又宽阔的舞台中央,默然相对,彼此慰藉。
我明明已长大,可是,我还没长大到能让父亲安享晚年,父亲却已病得不成样子了。
好在父亲的病渐渐好转,我们家的新生活也一页页翻开。后来,我毕业分配到一所中学教书,结了婚,有了娃,生活渐渐稳定。有一天,我和父亲商量,准备报考博士,如果考上,要再念几年。父亲眼睛一亮,说,考吧,趁年轻,该刻苦就刻苦。
备考期间的许多时候,我把孩子交给父亲带。孩子调皮,天天拉着他去村里阿叔家看奶羊和羊羔,父亲完全听了孩子的指挥,我笑他这是“使牛给牛做主”,父亲一笑,表示默认。后来,父亲干脆就自己养了两只母羊,说这样既可以看羊,也可以吃羊奶,羊奶多了还可以卖点钱。再后来,父亲不顾我们的反对和欠安的身体,在家养起几十只猪。修猪圈,买猪仔,备饲料,防病疫,除了把养大的一部分猪卖掉,还把其中几只小猪养成母猪。母猪又生了猪仔,他细心照料,剪牙,保温,打疫苗,去根,然后又把猪仔养成大猪……一大堆的琐事全都揽在自己身上。
为了备考博士,我咬紧牙关,默默坚持。白天上课批作业,晚上督修备完课,我还要安排时间背单词、做复习笔记、看参考书、做练习,常常到三四点才能休息,第二天又要起来看学生早读。有几年时间,大年三十吃完年夜饭,我都把自己关到邻居家的一间屋子里背单词、复习文学史,正月初一我早起又读到十点多,才陪老婆去丈母娘家拜年。有一次去浙大考试,没有买到卧铺票,我硬是坐了一个通宵的火车到达杭州,第二天一早从火车站坐公交到浙大门口,把行李寄在门房那边就直奔考场。去苏州大学考试,没有订到附近的旅店,我和临时认识的一起考试的一位南通大学老师凑合住了两个晚上。备考几年,我几次到复旦大学的旧书店,淘了几箱书籍资料,把里面的有关知识整理到笔记本。我一边工作一边备考,屡败屡试,不甘放弃。我憋足了劲,仿佛要和父亲比一比,看谁更刻苦,更能坚持。
可是,几年下来,我一直没有收到梦寐中的那张录取通知单,却收到了父亲的病危通知单。
那一年,父亲体内发现的癌细胞已经是四期了。那一年,考了八次博士之后,我告诉父亲,今年又没录上。父亲看了看挂着的吊瓶,没有言语。那一年,父亲在辗转多家医院,经过明知没有结果的艰难治疗后,带着遗憾离开了。
那一年,送走父亲,我又来到白塘。正值黄昏,游人散去,公园的门口冷冷清清,只有暖风轻拂,一只飞不起来的风筝,挂在树梢上随风挣扎。
梅园里的梅花多已凋谢,梅树脚下的土地被游人踩得凌乱不堪,残红遍地。梅树枝头,绿叶抽出,片红难觅。倒是映在湖面的树影,在夕阳残照里像一幅水墨画,颇有韵味。
春意已浓,我心却冰冷。我知道春天每年都会光临我们的世界,但未必都能温暖每个人的心灵。我也知道,梅花每年都会开放,但未必都能点亮每个人的春天。
忽然想起童年时父亲带给我们的欢乐,想起那年父亲带我看梅花的情景,想起那年和一朵梅花的形影相吊,想起一直默默鼓励我的父亲从此天人永隔,想起我的梦想像湖面的涟漪一样虚无缥缈,心中况味一时难以言表。我蓦然回首,看了一眼夕阳,夕阳那么美好,美好得令人无法亲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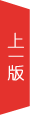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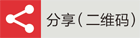
 前一期
前一期
 闽ICP备06035371号 闽公网安备35030002001038号
闽ICP备06035371号 闽公网安备35030002001038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