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宝洪
家在江南水乡,家门口就是一大片稻田。我5岁那年秋天某日,生产队出工在我家门口的稻田割禾,个子比谷箩高不了多少的我,提着一个灌满了温开水的竹制茶筒,蹀躞着细碎的小步,跟在母亲身后,来到稻田,参加“义务劳动”。
稻谷金黄,田野飘香,沉甸甸的稻穗在风中风姿绰约地摇摆身段,母亲弯着腰,手握锋利的锯镰,麻利地割禾。母亲每割一小束禾,就把禾捆成一小把,放在地上。我把茶筒放在田坎上阴凉处,贴在母亲的身边,捡拾母亲不小心掉落的稻穗,把母亲捆成小把的禾秆抱起来,堆放在田塍上,或直接搬到打谷机边。秋阳似火,晒得人一身是汗,母亲脸上的汗珠时不时落进土里,但没有放慢劳作的节奏,我伸出小手给母亲擦汗,母亲问我渴不渴,我嗯了一声,母亲就起身来到田塍边,从田坎里取出茶筒。母亲怕我喝水太急被水噎着,也担心我抓不稳茶筒,她双手端着茶筒,把茶筒的口对着我的嘴,让我喝水。我喝完了,母亲就抓起茶筒,仰着脖子,大口大口地喝水。接着,又去忙她的活计。
打谷机的欢叫声像磁铁一样吸引着我,我离开母亲的视线,来到打谷机旁边,着迷地看着打谷机的齿轮在飞速旋转,看了一会,我悄悄地把我的小脚踩上打谷机的踏板,惬意地踩,累了就歇一会,再踩。踏打谷机的是一个健硕的少妇,不到30岁,按辈分是我的叔婆,我叫她顺秀婆。顺秀婆发现我在踩打谷机,就让我一边玩耍去。她担心我的小脚跟不上打谷机旋转的频率,生怕给我带来意外的伤害。
一坵稻田的禾收割完毕后,打谷机要移动到另一坵稻田打谷。前面一人拉纤般在拖和打谷机连在一起的斗房,顺秀婆在后推打谷机的挡板。我看他俩颇为吃力,就上前帮顺秀婆推打谷机,打谷机在滑下田坎进入一坵稻田时,我被惯性带着,摔下了田坎,疼得当场就晕过去。
我醒来后,发现自己躺在公社卫生院的病床上,腿上还上了夹板敷着石膏,母亲正关切地、慈爱地、忧戚地端详着我。我出院后,站立和走路都极为艰难,但还是喜欢四肢并用爬到收割过后的稻田去玩。在田野玩耍时,有小伙伴淘气地笑我像狗一样爬来爬去,甚至模仿我爬行的样子,我呵呵笑着,继续和伙伴们做游戏。
那次割禾,是我参加的首次农事,也是我最早的人生记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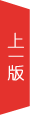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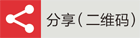
 前一期
前一期

 闽ICP备06035371号 闽公网安备35030002001038号
闽ICP备06035371号 闽公网安备35030002001038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