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闲
原莆田县第二十中学,在常太当地乡亲口语中多简称“二十中”,后来更名为“常太中学”。
对于“二十中”,当年民间的一段顺口溜,虽然不免夸张讥诮,但也约略可知其校园校貌、校风校纪。
顺口溜大致内容是:
常太二十中,
无门共无窗,
找饭罐、人相撞,
谈恋爱、会火熏,
用犁头、作敲钟,
水库死人齐逐凶,
先生肉饭用称分……
我们写《我爱我的学校》之类的作文时,开头都喜欢用“银山脚下,东圳之滨”之类诗句,倒也贴切。
常太中学的后山名唤银山,面临东圳水库,风景这边独好。但是当时的办学条件极其艰难,设备简陋,往返不便,却是在这里任教老师的心头之痛。所以,这里便成了对教师惩罚性分配或调动的“流放地”。
正如“江山不幸诗人幸”,我在常太中学读书时,也是欣逢“先生不幸学生幸”的难忘时光。
根据当时受教的情形与收获,以及后来慢慢了解的积累,我现在可以作出一个基本判断:当年,至少是1973—1975年那个时间段,在常太中学任教的,都是很了不起的教师,有些还是城里名校的名师。可能正是因为这里是“流放地”,那时城里那些“知识越多越反动”的“几类分子”就被谪贬于斯,构成一派本地风光,虽然“无门无窗”,但也藏龙卧虎,凤翔鹤舞。
又是一年教师节。为感念师恩,我意图写一组文字来纪念在“无门无窗”里教书的先生。先从吴鸿池老师写起。
我和吴先生没有私交,先生也可能不知道他所教的一堆学生中有一个“我”存在。他对所有学生都可能视而不见,所有学生对他也远之而未必敬。
原因很简单:他似乎很怕。怕什么?他自己知道,或者不知道,只表现为保持距离,尽可能节省交流语言。
这还不是真正的深层次的原因。有人透露,他的“家庭成分很高”。这个“高”逼迫他必须以“低”的姿态存世。
吴先生与我,在那时可能彼此互为“不存在”,但在数十年后,他却时不时存在于我的心灵意识中,时不时存在于我的文字言语中。
前数天,我参加一场诗词朗诵会。在整场朗诵会中,唯一我选择了用“方言吟诵”的形式。效果如何,我不能自己评定,但形式肯定是独特的、唯一的。在吟诵中,我仿佛有吴先生附体,包括我的摇头晃脑和抑扬顿挫。
前数年,我参加省图书馆承办的《国家图书馆方言吟诵抢救性记录》项目的研讨会,应会议方要求,我在会上用莆仙方言吟诵了《木兰辞》全诗、荀子《劝学篇》片段。吟诵甫毕,一位来自厦门的与会老先生(看上去有八十多岁)马上发表点评,说这是“正宗官话”、是“纯粹文读音”、是“古代的普通话”云云。
我不知道这些术语概念,也不知道老先生是否专业内行。但我可以肯定,我只是在模仿重现吴先生而已!
某次偶然间与老伴聊起中学教师,论及吴鸿池老师,老伴美人一笑,倾倒了我。
她说,她们女同学最不喜欢吴先生上课。不过,她们可以从吴先生走进教室的那一瞬间,判断出先生这一节课要讲什么内容。如果先生神采飞扬,激情洋溢,那一定是要讲古文了。
当时,先生教我们《木兰辞》,第一句“唧唧复唧唧”,他提出了“复”字要读“伏”的第几声调(现在我知道应该是第五声?),不能读“伏”或者“福”,会被人耻笑,然后他自己先笑起来。
后来又教到“雨后复斜阳,关山阵阵苍”,他又强调了“复”的读法。
有一次,我混在莆仙戏民间音乐班里滥竽充数,看到一首【春复春】,我不经意间读出曲牌。翁老先生当即点评,他说他第一个听到我的正确读法,然后又调查我从何处学来。我谦恭而惶恐地回翁老先生问话,说是我中学时的一位吴老师教的。
吴老师不苟言笑,但偶尔一笑,却能笑出娃娃脸。他的形貌装饰让我想到另一位先生,那就是鲁迅先生的藤野先生。鲁迅先生在《藤野先生》一文中描写藤野先生,和我们的吴先生,可以算是“相反”的款式。藤野先生长得有些黑瘦,八字胡须,冬天旧外套寒颤颤。我们的吴老师微胖、白晳,脸总刮得洁净,冬天短棉袄,靠近他就觉得春光和煦。但是他们应该都符合散文的特点,即神似而形不似,形散而神不散。
吴先生讲课时的“神”,全部写在眼镜后面那双圆圆的眼睛上。讲到得意处,他的眼眶会湿润,一如午后的东圳水库,波光粼粼,明灭闪烁。比如他读《劝学》,当读到“君子博学而日参省乎己,则知明而行无过矣”时,整个教室显得空荡荡的,他的声音则如空谷足音。也许是受他眼中波光的映射润泽,我至今还能勉强背诵他教过的《劝学》,而且是用莆仙方言背诵。
我们那时候的毕业差不多类似作鸟兽散,并没有哪位先生送给我一张照片,背面写着“惜别”二字;也没有轻轻地我走了,向银山青松东圳波光挥一挥手;更不会有人唱“今宵别梦寒”,然后男生女生抱头痛哭……
我们的毕业就是放假回家参加生产劳动,就是记清楚被服草荐脸盆毛巾牙杯饭罐全部带回家,不能丢下一件。
我对母校唯一的怨言就是,没有发给我们毕业证书,连肄业文凭也没有。以现在流行的“形式”主义审查,我们那一届上的是“假高中”,或者根本就没有上过高中。
幸亏,吴鸿池老师教给我的那些语文知识,我至今受用。由此,我确信曾经高中毕业,至少是高中语文单科结业。
感恩吴先生,让我当一回高中生。
吴先生教书,在往时以至于现时,似乎都没有什么好评。但在几十年以后,在我无聊读闲书中,似乎发现了他是依“法”施教的。他是依规依矩地传道授业解惑的,“句读之不知,惑之不解”,他都没有轻率放过。
古人的“教案”显示,讲解一篇文章,必须有读、说、注、解、讲诸多环节或顺序,吴先生总在不着痕迹地实行。
不知道现今的课堂语文教学,是否亦复如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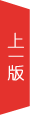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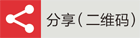
 前一期
前一期
 闽ICP备06035371号 闽公网安备35030002001038号
闽ICP备06035371号 闽公网安备35030002001038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