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智勇
小时候跟我妈去看过一场电影,什么内容如今几乎空白,只约略知道是刑侦类的,记忆中晃动着白色警服、大盖帽和边三轮。片名倒是记得清楚,叫《第十一个弹孔》。后来百度了一下,才知道其实连片名也记混了,是《第十个弹孔》。
我不知道为什么会记成十一个,这该死的记忆,骗了我几十年。唯一能记真切的,是为了这场电影,我妈蹬着脚踏车载我一起去往城关的旅程。她是那么地喜欢电影,不惜长路迢迢。她喜欢刘晓庆、高仓健和朱时茂们,家里有《大众电影》《电影之友》,我偶尔也翻,并没有被呵斥着要去做作业。
她骑着新买的“永久”牌自行车,驮着我,一圈一圈地蹬,蹬在坑洼的土路上,小心翼翼地避开大大小小的水坑,七扭八扭,直至上了柏油路,才稳当了下来。
有时碰到不好对付的路况,她会急急捏闸,再把右腿匆匆收了掠过还套着泡泡膜的车梁,像跳高运动员般落地,之后才把车子停稳,就那么双手扶着车把,站得笔直。她至今还不习惯原地撑腿停车,哪怕车子再矮。
偶尔她也会叫我跳下车,待自己在平路上骑稳了,再让我小跑着跳回去。我总是跳得相当轻盈,像片树叶般落在后座。对于这点,她相当满意。
跳车也是她教的。一开始我不敢跳,她就怂恿:“打捕人要有打捕人的样子!”她有很多事,在性别上分得很清的,譬如男人一定得勇敢冒进,会修点电器之类——起码懂得换灯泡而不是去学织毛衣,可惜我两样都没学会。
终归是她车技不好,我爸就从来没那么慌忙过。他会一手夹烟,一手握扶手,很从容地蹬,无论多远的路,从没叫我跳过车。
但是我爸又很少骑车载过我,记忆中好像才两三次。
我享受着被我妈载着旅行的过程。是的,旅行。虽然从老家龙坂到城关,如今看来近在咫尺,但是对于一辆单车和不那么平坦的路面来说,是个不短的旅程。
我那时并没有抱着她的腰,而是两只手抓住坐垫下的弹簧,我不知道为什么要那么做,是我妈怕影响到她的骑行不让我搂着,还是那样抓着我自己更容易平衡?也许都有吧,反正我一遍遍地回想,这个记忆是真切的。
我还喜欢往路两边瞎看,稻田,炊烟,一惊一乍的麻雀和丑陋的稻草人。微风吹拂,相当舒服。那时电杆和房子远不如今天密集,远山绵长神秘,沟渠就在眼皮底下,水流欢快。
柏油路一段一段后退,有时看得我昏昏欲睡。
“别爱睏,”我妈总会适时转头说,“担心,别掉下去!”
我说我不会,我抓着弹簧呢。
“别睏!很快就到了。”我妈又说,“脚别又伸到轮子里。”这回我吓得下意识往外撇了撇腿——我被绞过一回,知道那些亮晶晶筋条的厉害。
我妈能转头跟我说话,担心这那的时候,通常是骑在最好的路段。她骑得轻盈,似乎不用使上多大劲儿。风有时把她的白色布笠吹了下来,吊在后背一荡一荡。我喜欢去玩这种三折两拗能缩成圆圈的布笠,里头钢丝儿弹力十足,呼一下弹开,十分带劲。
过了大济街,我知道我妈要开始唱歌了。
“军港的夜,静悄悄,海浪把战舰轻轻地摇……年轻的水兵,头枕着波涛,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她绷直上半身,载着她最小的孩子,昂着头开心地唱着,有时也忘记歌词。歌声偶尔被并行的拖拉机巨大的噪音盖过,切断又续上,像一台信号不好的收音机。
“老师现时教你们唱什么歌?”她转头问。
“《卖报歌》。”
“啦啦啦,啦啦啦,我是卖报的小行家。”她轻轻哼唱了起来,“是不是这样?”
“嗯。还有《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
“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继承革命先辈的光荣传统,爱祖国,爱人民……”我妈换了一种嘹亮高亢的嗓音,兴之所至,还按了一串响铃。
我继续左顾右盼,寻找风景。然后,她突然转头说:“数学老师说你上课老是开小差,有吗?”
我想说我没有,想说我只是听不懂。但是我没吭声。
“不懂就要举手问,胆子大一点!老师说你一站起来说话就脸红,有没有?”
我说我没有。事实上,我已经在开始脸红了。
她叹了口气,说:“男孩子终归要胆大一点的,别像床下的尿壶!你要能像你二姐那样就好了。”
我开始想我二姐到底是什么样子。她老是风风火火,敢跟任何人打架,一脸牛都敢顶撞的样子。
“明年就轮到我教你们班了。”我妈加重了语气,“得给我争气点!”
我说:“嗯,你教我们数学吗?”
“语文。”我妈说。
我有点失望。说:“妈,我们快到街路了吗?”
“穿过前面那个拱门,看到没?”我妈加速踩了几下,指着不远处的一个拱门说,“一过去就是街路了。”
那时候我们管城关叫“街路”,拱门似乎是区隔街路与乡下的第一个地标。如果恰逢榨季,会有拉满甘蔗的火车从上面“咣当咣当”驶过。
车骑过拱门,短暂的黑暗之后,前方又复亮堂,明显地热闹了起来。
我妈说:“等你长大了,够得着了,就去学脚踏车,妈以后老了,要你驮着来街路。”我说:“我要学开拖拉机,跑得快,还能拉一车人。”我妈笑了,说:“拖拉机算什么,你以后要是读书,火箭都开得。”
时光荏苒。转眼我已半百,开滴滴也快5年了。我妈也活成了一个拿着退休金身边总有一群佛友的70多岁的老太太。
我知道她一开始对我跑滴滴很难释怀,有时遇到相熟的老友、儿时的那些阿姨问起我,她总是支支吾吾,随口几句搪塞了过去。我知道她曾对我寄予厚望,结果我却活成了现在这个样子。
我知道我们姐弟仨一个接一个没有读出像样的书来,就像一梭伤心的子弹,击中一向要强的她,留下一串难堪的弹孔。
好在时光渐渐慰藉了她,慢慢接受了我们平庸的样子。
她自己仍像年轻时那般“社牛”地存在。搬来城关不过十天半月,能跟整幢大楼的男女老少都能聊上天。有时我跟她一起从超市回来,先后进了楼洞,可我都到家半小时了,还没见她上来。
我只好“噌噌噌”下去找她。她果然就站在楼道,手里“哔哩啵啷”提着东西,跟一个下楼的阿姨聊得正欢。我闷声帮她提了东西上去,刚转过楼梯就听她跟人说:“嘿嘿,这是我仔哈,也不懂得问候你一声,随我那老头子!”
我就觉得我爸瘦弱的背上又添了一口锅。她永远不懂得社恐,像白天不懂夜的黑。
她仍热衷旅行,不时跟她的老姐妹们出现在一些景区,穿着显眼的印有“南无阿弥陀佛”的红马甲和红帽子,举着小红旗,穿梭在人海中。
回来就把照片和视频整理,往微信群里发。或是坐在小板凳上,认真地戴上老花镜,对着手机跟没法去的朋友分享旅行的心得,说“下回再一起去”,说“有你们这帮老姐妹真好”。
有时她跟人聊着聊着,会突然对我说:“哎呀,给忘了,冰箱里还有半只鸭放好久了,得拿出来,不吃要坏了。”
无缝切换。我喜欢我妈这种风格,总有莫名的喜感。
时至今日,我仍会时不时潜回时光中,去回味那段旅程。回程里,夕阳染红天空,我在后座睡着了。
有次我开车送她,不经意跟她聊起这段旅程,一帧一帧回放。我妈总是说:“有吗?不记得了,你惦记的跟我的不一样。”
我觉得她说得对。
或许人生就是这样,相同的旅程,会有不同的风景。可只要彼此还在路上,一切都是美好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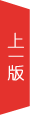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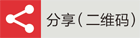
 前一期
前一期
 闽ICP备06035371号 闽公网安备35030002001038号
闽ICP备06035371号 闽公网安备35030002001038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