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国太
往后坡埕方向出李巷,巷口左侧一座小庙,乍一看,会错认成土地庙。庙门朝外一副对联:“礼佛诵冈陵寿算,考文正泗水渊源。”横批:“指迷津。”字多繁体,颇费辨认。因为知道此处供奉“泗州文佛”,与“泗水渊源”和“冈陵寿算”相印证,也可以确认,对联既点明佛与泗水的渊源,也表达诵经礼佛以求延年益寿的愿望。这与今闲先生所记稍有差别。今闲的《萝苜田里的泗州文佛们》,记录了此处小庙的联句,横批同是“指迷津”,但对联不同:音传泗水指迷津,曲度云峰归觉路。大概对联一年一换,所以所见不同。不过,也可以看出,信仰文佛者颇多能人,能拟出一二表情达意又辞简意足的佳句来。
今闲、阿鲁乃至前哲陈长城们,先后研究了泗州文佛现象,正是莆田民间的“佛公”信仰。在街头巷尾、三岔路口的墙上凿开一个小神龛以供奉,夏季一到,皓月当空、更深夜静之时,往往有老少妇女来到神龛前,焚香祷告,问卜求卦,祈求指点迷津,这便是所谓“听佛卦”。清代周亮工《闽小记》、施鸿葆《闽杂记·泗州文佛》都有相关记载。阿鲁是涵江老文史专家程德鲁,他撰文对“佛公”信仰作了介绍,文中引用宋人钱易《南部新书》一句话:“王延彬(王潮弟王审邽之子)独据建州,称伪号,一日大设,为伶官作戏云:‘只闻有泗州和尚,不见有五县天子。’”事在五代后晋出帝(943—946年)在位时,南唐伶官敢以此嘲讽土皇帝,说明彼时“佛公”已经传到福建。
萝苜田里另有几座泗州文佛,后郊路上、旺菜池畔、廿五坎旁,都有。据说泗州文佛是观音菩萨化身,善治水。萝苜田水网密布,过去人们仰赖文佛治水,大概可以理解。
我本打算把这四处的文佛们看一个遍,可是走着走着,便被另外的景象吸引了。在萝苜田这片不很大的空间里,竟然隐藏着众多的宫、庙、庵、堂,还有宗族祠堂。妈祖行宫自不待言。萝苜田不仅依赖三江口港开展对外海上贸易,还通过内河,北连梧塘,西向城关,还有黄石、北高、仙游等地,频繁地往来运输客货,人们便多建妈祖宫,祈求妈祖保佑水上人货平安。据说,宫口河的得名就源于此。明代时,河的北岸就有一座奉祀妈祖的灵慈宫。霞徐历史上曾有7座妈祖宫,现在还有“旧宫”“大宫”“新宫”加以区别。另外还如延宁宫、前林天后宫,也都年代久远。
萝苜田历史文化街区东起霞徐街,南至集奎沟南岸,西抵白塘街,北界北宫口路,包括了青年、延宁、楼下、涵西、保尾、前街、霞徐社区和集奎村,总面积约850亩。走过大街小巷,除了以上的妈祖宫和文佛庙,有不少佛寺如湧林庵、清德堂、仁德堂、真华堂、义德堂;有道教场所,田尾的兴贤社,苍头社即南庄社,武当殿、玉华殿、北极殿,廿五坎北面还有龙楼社。
我已经记不清自己多少次到萝苜田。有一次走到保尾街背面,不经意间抬头一看,“善德堂”三字映入眼帘。印象中,我曾编过善德堂的文章,却一时记不清具体内容。正在踟蹰间,堂门内一位年过五旬的男子,推着自行车将要出门。互相对视一眼,我下意识地说:“这是善德堂?”他温煦一笑,答道:“善德堂。”我看他摆出欢迎参观的样子。不知为何,我婉拒了。后来,我试图给自己找个解释,可能是心中无底不敢贸然造访吧。
回来后,急急查阅资料,才知道,善德堂是三一教堂祠,祠内有末代进士张琴的两副对联,一为隶书楹联:徘徊云影天光外,自在清风明月中。一为篆书联:心性精微弁藉外,乾坤浩荡一丸中。还是张琴老先生厉害。看后面这副联,“弁”是“辨”的通假字。上联道出,三一教融合儒家存心养性、佛家明心见性、道家修心炼性三重维度;而下联,“一丸”又与儒、释、道三教皆有关,展现了“三教殊途同归”的教义特征。1930年冬,涵江发生特大火灾,“延烧二百余户”,几乎毁了当时涵江最繁华的商业地带。为了筹集救灾资金,涵江士绅组织“涵江火灾善后委员会”,向全国政界名人、知名画家、书法家征集援助救灾的书画作品5000多件。1932年,涵江救火会在善德堂成立,为保护涵江人民的生命财产作出很大贡献。
以“善”“德”为名,或许正是三一教所奉行的。三一教是明代莆田人林兆恩创立的儒、道、释三教合一的民间信仰。林兆恩,号龙江,一生做了大量的慈善活动,《莆田通史》载:仅嘉靖四十年(1561年)至嘉靖四十三年(1564年),他组织门徒先后六次收埋和火化因倭乱、瘟疫死亡之人的尸体23000多具,火化白骨无数,有效地抑制了瘟疫的流行。其无私奉献的大爱精神和急公好义的善举,得到时人的交口称赞和后世的景仰。
是的,我生活的南北洋平原,很容易就听到一些“三教先生”的消息。当我们视线越过卢溪,投向一片雄伟的建筑,便看到萝苜田里有名的建筑:杨氏民居。这里曾经是三一教林龙江四大门徒之一卢文辉的故宅所在。
我记起在草屿岛上,看见过另一位三一教门徒朱慧虚的墓茔。朱慧虚原名朱逢时,慧虚是道号,拜林龙江为师。草屿岛在北高汀江村外木兰溪入海口,靠一条人工筑就的水泥路连接,这条长660米的路,涨潮时隐于海水下,退潮时它卧在灰黑的、起伏铺展的泥滩之上,宛如灵动的虬龙,又似一根系带,一端接着大陆,一端放飞着草屿岛。我曾经多次骑车上岛,岛上面向对岸陆地有片庙宇,唤作“心海祠”,心海、心海,心之海,广阔、浩瀚、无极,多变幻、难捉摸、善容纳。我骑车离去,沿着一条人工修筑的笔直的海堤骑行,嘴里念叨“心海”,突然觉得兴味盎然、妙趣无穷。直到最近,我因为写萝苜田,四处翻阅资料,才知道,朱逢时便著有《心海真经》一卷。而草屿岛的“心海祠”,供奉的是林龙江。一座祠、一座岛、一片海、一条时隐时现的路,可否与“心海”联系起来,来解读“心中的宇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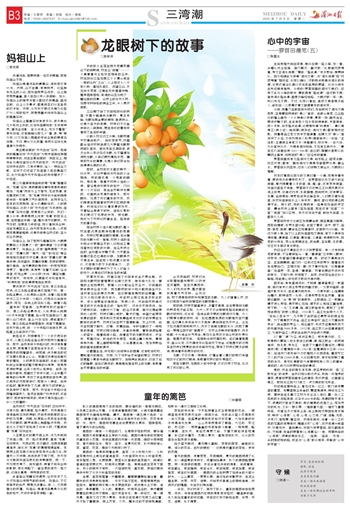




 前一期
前一期
 闽ICP备06035371号 闽公网安备35030002001038号
闽ICP备06035371号 闽公网安备35030002001038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