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忠瑜
天热得紧,远处,稻浪翻腾着,正酝酿着成熟,村里的男女老少皆等待着“双抢”时节的号角吹响。我的父亲早已将那把镰刀取了出来,在屋前檐下静静擦拭着。
镰刀样子并不出奇,木柄油光水滑,柄端微微弯曲,如人劳作久了微微弓起的脊背。刀叶弯弯,刀尖则锐利如鹰喙,寒光凛凛。父亲手掌厚大,指节粗壮,握刀柄之处,早被磨得光滑柔顺,微微凹陷下去,仿佛镰刀已在他手中长成了身体的一部分。
割稻子前需打磨镰刀,父亲搬来一块青灰色的磨刀石,蹲坐在门槛前,撩些清水泼在石上,弯腰俯身,将镰刀在石上推动起来。父亲身体微微前倾,双臂前后移动,动作稳健有力,刀与石相触,发出“沙沙”的声响,单调而执拗。铁腥气混着石沫的味道,在空气里弥散开来,如同泥土被犁开时的气息。磨刀石中间渐渐被磨出一条凹陷的浅槽,镰刀每划过一次,便留下一道微白的水痕。
镰刀既磨得锋利了,“双抢”便开始了。镰刀与稻秆相触,发出“沙沙”的轻响,仿佛镰刀在从容进食。镰刀在父亲手中,宛如有了生命,它“吃”稻秆,刀锋过处,稻秆便驯顺倒下。然而,烈日当空,时间紧迫,镰刀“吃”得越来越急促,声音也由“沙沙”变成“咔嚓咔嚓”,最后竟成了“咯吱咯吱”的啃咬声。镰刀也似乎渐渐“吃撑”了,刀锋卷起,钝了,再不复初时的锋利。
父亲弓着背,脊梁沟里汗水蜿蜒而下,在背上犁出几道湿痕。母亲在正午时送饭至田头,饭是粗米饭,菜不过咸菜之类,盛在粗瓷碗中。父亲席地而坐,匆匆扒几口饭,镰刀就倚在田埂边,刀刃映着白炽的阳光,闪闪烁烁,像是一弯被遗落在尘土的小月亮。
天色渐晚,父亲方拖着疲惫身子归来,镰刀挂在腰间,随脚步而晃动,刀锋上还沾着几茎稻穗的碎屑。到家后,父亲把镰刀挂于近旁土墙上。灯光在刀锋上跳跃,投映于墙壁,竟使小小的屋里显出几分清冷而温柔的明亮来。
后来,父亲老了,镰刀也渐渐闲置在角落。我偶然从老屋杂物堆中翻出它来,刀身早已裹着一层暗红铁锈,木柄也干裂出许多细纹,显出朽旧。我轻轻摩挲着刀身,指尖掠过那锈迹斑斑的弯月,仿佛触碰着一段凝固的岁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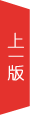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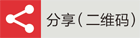
 前一期
前一期
 闽ICP备06035371号 闽公网安备35030002001038号
闽ICP备06035371号 闽公网安备35030002001038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