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飞
啖一颗荔枝,呷一片羊肉,听一声蝉鸣,看晚风轻拂古厝燕尾脊的檐角……大暑的寻常滋味,在莆田涵江阿海家的老厝里。
“阿弟,食羊肉啦!”阿海妈嘹亮的莆田腔,带着不容分说的热乎劲,直直撞进耳膜。七月的盛夏,天地就是一口滚烫的蒸笼。我这初来乍到的“客边人”,坐在阿海家幽深的老厝堂屋里,后背衣衫早被汗水洇透,粘在竹椅上,动弹不得。桌中央,一砂锅羊肉汤正“咕嘟咕嘟”翻滚得忘情,汤面浮着晶亮的油星,姜片、当归、枸杞在浓汤里载沉载浮。那股子香气,霸道地攻城略地,热浪直扑人脸,仿佛要把空气都点燃。我心底直犯嘀咕:这天,热得人恨不得钻进冰窖,还喝这烈火烹油的汤?这不是火上浇油么!
正惶惑间,一碗晶莹的剥过壳的荔枝忽地递到眼前。阿海妈笑着,“食几粒,先解解燥!”
我依言拈起一颗冰荔送入口中,清甜如蜜的汁水瞬间在齿间爆裂开,一股清凉直透心脾,仿佛给燥热得几近冒烟的五脏六腑,兜头淋了一场酣畅淋漓的甘霖。这冰凉的甜,与对面砂锅里升腾的羊肉浓腴的热气,在溽热凝滞的空气里无声交战、交融,竟奇异地熨帖了我这“客边人”的惶然与疏离。
“趁热吃!”阿海端起一碗滚烫的羊汤,不容分说塞进我手里,“汗出透,暑气就败了!”汤碗烫手,镜片瞬间被白茫茫的雾气笼罩。我屏住呼吸,啜饮一口。一股滚烫的热线,直冲而下,瞬间,额角、颈后、脊背的汗珠争先恐后奔涌而出,畅快淋漓!原来这就说“以热攻热”呀。
此时,窗外古榕上的知了骤然发力,声浪一阵高过一阵,应和着砂锅里汤汁“噗噗”地沸腾喘息,仿佛在合奏一首古老而炽烈的夏日战歌。
一碗热汤见底,汗也出透了,衣衫湿透,贴在身上,却有种奇异的松快。阿海妈适时递来一杯深褐色的凉茶,碗底沉着几片不知名的草叶。喝一口,微苦,旋即回甘,草木的清气在唇齿间弥漫。穿堂风不知何时悄然潜入,徐徐而过,温柔地吹干汗湿的衣衫,留下凉滑的触感紧贴着皮肤。先前的闷热与滞重,仿佛真被那场酣畅淋漓的汗水席卷而去,通体只剩下一种难以言喻的轻快与通透。
“食饱未?”阿海笑着问我。这句再寻常不过的莆田问候,此刻听来,却像檐角那缕拂过燕尾脊的晚风,轻轻柔柔,拂过心坎。原来那碗滚烫的羊汤喝下去,喝通的不仅是闭塞的毛孔,也悄然融化了横亘在异乡客与本土乡音之间那层无形的坚冰。
回到南京,梧桐树上震耳的蝉鸣依旧。门铃骤响,一个泡沫箱送到手中——竟是阿海从莆田寄来的荔枝!冰袋间,簇簇鲜红如玛瑙,倔强地保持着千里之外枝头的新鲜。便签上是熟悉的、带着几分笨拙却无比真诚的字迹:“阿弟,荔枝正当时,冰着食。”
剥开一颗,莹白如玉的果肉裹着清冽甘甜的汁水入口,瞬间,莆田那个溽热得令人窒息的午后便汹涌而至,无比鲜活:堂屋天井里灼人的白晃晃阳光、砂锅里羊汤翻滚的浓香、阿海眼中跳动的热切光芒、那滚烫如烙铁的莆田乡音……
这异乡的寻常滋味,一旦尝过,便如同认取了一条隐秘的归途。千里迢迢寄来的荔枝,何止是时令鲜果?它是一把钥匙,带着古厝檐角的温度与海风的气息,熬成了心底最难消解的“荔火”滋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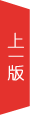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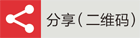
 前一期
前一期
 闽ICP备06035371号 闽公网安备35030002001038号
闽ICP备06035371号 闽公网安备35030002001038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