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披星
我就是那个拾贝人。这看起来有点可笑,一个胡子拉碴的中年男人竟然是海边捡拾贝壳的人,而且还有点乐此不疲。这在外人看来,多少有点张飞绣花的场面感吧。还好沙滩够大,大到几乎每个人,哪怕再高大的人,在这片浩瀚的海洋背景下,也会变成一个细长的身影。海洋和海滩一样,它总能让置身其中的人不自觉间就变小了。这也给了我某种自在,也挺好的。
蚝类的、贝类的、螺类的、蛤类的……随便一个沙滩都有不少。这大概算是大海最微小的遗留物了。想来这贝壳,都已然经历了生命前半段的旅程,它们遗留下这么一个或一片坚硬的外壳,成了沙滩的点缀,传递着海的讯息。
看到贝壳,我总会萌生一种好奇,总要去想每个贝壳到底在海里经历了什么?是惊涛骇浪的一生,还是随波逐流的旅程?是不断抗击潮流的翻腾,还是在海底的暗流中,无声地刻画着自己的波纹?这些联想既奇异又深远,仿佛能穿越无垠的海洋。贝壳微小,自然是沧海一粟。它们也可以是明亮的、完整的、美丽的,甚至是神秘而迷离的。它见过的必定远远比我要多。它经历深渊和暗礁、洋流和漩涡,必定也见过那些远洋的船、离散的人、跨越洋流的寻觅、鱼类的爱情和等待的孤崖吧?
先有鱼,还是先有贝类呢?贝类依附于礁石之上,似乎应该先有贝吧。我不知道。这拥有300年历史的城池,其基石却是历经3亿年风雨的石头呢。那么,贝类也是吧?亿万年之前,它们便悠然地在深海中游弋,或浮或潜,自由穿梭于这海洋和沙滩之间。
贝类的美丑其实不存在,存在的是人类自身对美丑的认知。我把经常看到的花蛤类都舍弃掉,觉得它不美,原因就是经常看到也吃到它们,就觉得它们太像一个食物的盛盘了。那些生蚝被剔肉后遗弃的壳状贝类,看起来也十分粗俗,而且有些刺手,就像是贝类中的蛮横之徒。所以,我寻觅的,是一些我认为美丽的贝类——它们似乎都带有一种梦幻般的气质。细细看来,壳上都会有时间的缝隙,光阴的裂痕,洋流的磨砺,海洋赋予的斑斓色调……可以说,它们的颜色跟天空的色调也是对应的,又或者说,正是天空和海洋共同塑造了它们的色彩。
贝类无法细究,它必定是有无数种的颜色。这就像海洋有无数种颜色一样。灰的,白的,蓝的,黄的,还有晚霞色、彩云色、层层叠叠的过渡色……这些都是海洋留下的印记;偶尔还能发现那些令人叹为观止的美丽螺贝。这一切无不让人惊叹于海洋的创造力、流水的力量,以及那无以名状的惊人美感。
有一次,捡回的贝壳两天后竟然发现有寄居蟹臭在里面了,家人被臭味熏得颇有抱怨。这是我的疏忽,没有发现螺壳内暗藏的生命,便将它带回了家中,无意间伤害了小动物。那几只蟹,从沙滩和海洋的气息中被带到了干燥的人类居所里,很快就陷入了万劫不复的境地。想来,这还是因为人类的占有欲在作祟吧——多数还是以美之名。
我也不知道贝壳类捡回去有什么用。几个在花盆里,有的在房间角落,在电视柜边上,在某些看不到的地方……当然都是无用的。可它的无用之用在于你会在某个不经意的转角,不经意的转眼间看到它。这就是生活中平凡又奇特的一瞬了,微白的、清亮的一瞬。
贝壳当然也有实用的一面。我知道,石灰的主要成分就是由贝类烧制而成。这小小的硬壳,焚化之后也成了房屋的内饰。房间里,有些是看得见的贝壳,而那些看不见的贝壳,它们已修炼成了粉末,被涂抹成墙壁上那清清白白的一片空间。这自然的轮转中,蕴含着自然的神奇。
在海边的拾荒心态,也是让人迷恋的。海边总有捡塑料的人、捡铁器的人、捡麻绳的人、捡石头的人等等;夏季,海边人更多些,有捕蟹的人、电虾的人、拾鲜活贝类的人、挖沙蛎的人……这些拾荒者,为沙滩注入了的生机——也正因如此,每片沙滩都有了不被遗忘的理由。我们目的各异,却都依赖于海洋此刻裸露的片段。这份裸露,既是遗留,也是恩赐。我们这些拾荒者总会时不时地站起身来,看看远方锚泊的船只。我们看云的时候少,看船的时候多。
一沙一世界,这无数的沙才组合成一片滩。贝壳静卧在沙上面,也只是比沙要明亮一点点;算起来,可能更多的贝壳都已经化成了沙粒。与沙为伴,即使处于低洼之地,也能绽放出属于自己的明亮,这已然很好了。在低洼之处,甚至在阴暗之中,也可以悄无声息地散发着光亮,这便是贝壳一份微小的梦想了。
那些被拾起的贝壳,都已褪去了肉身,变得洁白而细腻,恰似时间留下的珍贵舍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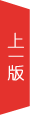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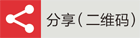
 前一期
前一期

 闽ICP备06035371号 闽公网安备35030002001038号
闽ICP备06035371号 闽公网安备35030002001038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