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剑芳
我一直笃定地认为,一所学校的灵魂,往往藏在三样东西里:古屋的褶皱、古树的年轮,以及那些在树影里走过的青春。
在莆田一中旧校区学习过的同学都会有这样的经历:生物课时,老师会骄傲地说,学校有棵种子植物中最古老的“活化石”银杏树。这棵银杏树,高大葱郁,如果你刚步入一中的校门,抬起头来一眼就能望见它。学生时代,我对银杏树的扇形叶子甚感兴趣,偶尔捡拾一片大风刮落的绿叶夹在书中。数月后,竟发现那抹青翠已悄然幻化成满叶的金黄。现在回想,金秋时节,满树的金黄,是校园一景,但我却始终未感受到如终南山古观音禅寺内银杏古树“一树擎天,禅意满园”的有趣景观。究其原因,可能是当时学校在全校划分卫生责任区,各班值日生责任心强,地上哪怕留存一片叶子即是对班级集体荣誉的亵渎,因此可怜的银杏落叶无法抱团积淀,形成如今人们趋之若鹜的“落叶铺金毯”的绝美画面。
若要评选一中的校树,相信很多人会投票选择主教学楼西南角的那株参天巨榕,树高超五层之楼,虬曲的枝干如铁铸般向四面八方伸展,撑起一片华盖般的浓荫。繁茂的枝叶层层铺展,交织成密不透光的绿网。微风吹拂,在阳光的照射下,每一片叶子仿佛都跃动着岁月沉淀的生机。根盘龙踞,周边围有一块五米见方、一米来高的土台,土台四周砌以平整的长条巨石,其上恰可供人们休憩。巨榕似一位饱经沧桑的老者,与矗立在旁古朴厚重、全石外墙的主教学楼景致相融,共同勾勒出校园里一道恢宏的景致。
主教学楼前的操场边有一株白玉兰,树约三四米高,树冠宽阔呈伞状,枝干挺拔却略显清瘦。纵使盛夏叶茂时节,在校园内各种参天巨木面前可以说是其貌不扬,相形见绌。然而当早春的暖风拂过,这株看似平凡的白玉兰便悄然绽放出令人惊艳的洁白花朵,宛如枝头静立的初雪,傲立在晨光薄雾中。满树琼苞如雪色微碧,馥郁芬芳似兰草清幽。每日从宿舍楼横跨半个操场向主教学楼中间楼梯走去,路过白玉兰树,白玉兰的花香弥漫在整个空气中,由远及近花香渐次浓郁,醉人心脾。
一校三树,像极了校园里永不褪色的传承——老教师如银杏沉淀智慧,中年教师似榕树撑起天地,而年轻师长,恰似这早春的白玉兰,带着露水与朝气,在春风里绽放出一片片最绚烂的花朵。
高一那年,历史老师陈爱民成了我们的班主任。接手我们班之前,他大学毕业后才在初中担任了一两年的班主任,眉宇间还略带着几分青涩。或许处于相仿的年纪,陈爱民老师少了些年长教师的严肃与严厉,倒多了几分自由与包容。还处于单身的他以校为家,生活、学习上倒像是同学们的老大哥。现在翻看那时全班登顶九华山拍摄的照片,只见爱民老师年轻而亲切。他几乎完全融入同学们之中,让人乍一看,根本分不清哪位才是传道授业的老师。
教语文的程惠钦老师同样年轻,课堂里总是流淌着诗意与激情。记得讲授杜甫《望岳》那日,“岱宗夫如何?齐鲁青未了……”她直接在课堂上声情并茂地朗诵起青年杜甫这首富有朝气的五言古诗。惠钦老师一头秀发柔顺披肩,一边朗诵一边踱步,渐渐走到教室中央,声音温润又不失力度。那一刻,整间教室就是她表演的舞台;又仿佛那一刻,她与浪漫豪情的青年诗人同在,要带着我们一同攀越那“一览众山小”的绝顶。
更巧的是,教化学的年轻老师姚荔华,竟是我小学老师的孩子,原来时光真的会以某种神奇的方式,将两代人的教育故事悄然串联。当然还有其他的年轻老师,与年段里喜欢打球的同学熟络,经常在篮球场上一同挥洒青春力量,这份亦师亦友的情谊,如同一张张温暖的照片定格,编织成我们共同成长、永不褪色的记忆画卷。
一中的这群青年教师,如白玉兰一般,岁岁绽放,以芳华育桃李,亲手送走了一批又一批的毕业生。30年过去,如今的他们已如银杏苍劲,似巨榕参天,成为莆田教育界的名师。但在我的记忆里,他们永远定格在“那年玉兰花开”的早春,带着露水与朝气,芬芳了我的整个青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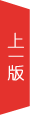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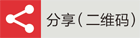
 前一期
前一期
 闽ICP备06035371号 闽公网安备35030002001038号
闽ICP备06035371号 闽公网安备35030002001038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