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清华
因为时间的流逝,我想起了一片甘蔗林;因为那一片甘蔗林,我迷失于时间的流逝。
那年冬天,我放寒假在家。黄昏,夕阳在西山的上空踯躅着,留恋地望着村庄。它像一位老画家一样,把每一座房子的屋顶,每一棵树的树梢,每一片水面用金黄色重新点染了一遍。
我在村西面的甘蔗林附近欣赏落日,忽然,看见一群大雁在甘蔗林上空盘旋着,鸣叫着。沙哑的叫声在甘蔗林的上空回响,让这片黄昏的甘蔗林显得更加深邃又神秘。
夕阳看见自己的得意之作又增添了几只灵动的大雁,非常满意,它把画作默默卷起,收藏在黑夜之中。
风吹起,甘蔗林整齐地起伏着,蔗叶摩挲,发出沙沙的响声,而响声下面,却让人觉得,有一片人间未有的温暖正在氤氲。大雁一只只从远处飞来,在空中盘旋,温柔地鸣叫,一种回家的温馨和自在,在它们轻盈的姿态中温婉地表达着。盘旋了一会儿,一只只大雁都落在了甘蔗林中。
我找来几个堂弟,商量着趁着晚上去甘蔗林抓大雁。
我们打着矿灯,蹑手蹑脚地进入甘蔗林,顺着畦沟,一点点往甘蔗林深处走去。
才走一段,就看见了大雁的踪迹:甘蔗畦的土地上,到处都是大雁的鸟粪,有的鸟粪甚至洒在蔗秆上,随处可见的羽毛七零八落地掉在地上。我们心中暗喜:这回肯定可以抓到许多大雁了。
把矿灯打着,继续前进,鸟屎和掉落的羽毛越来越多,我们的心跳也越来越快,总是想着等下会突然从哪里跳出一只大雁来。
我们在甘蔗林里越穿越深,可是仍然没有发现一只大雁。大家不禁有些泄气。我们试着摇动蔗秆,想着弄出一些动静来,吓出躲在暗处的大雁,可是不管怎么摇,也没有见到一只大雁,一直到我们从甘蔗林的这头穿到甘蔗林的那头,连大雁的踪影也没见着。我们很是纳闷,明明黄昏时看到它们都落在甘蔗林里,怎么会凭空消失了呢?
第二天黄昏,我和堂弟们特地来到甘蔗林边再次侦察,大家确认大雁都落在甘蔗林里,才放心地回去,准备晚上的再次行动。
这次的行动吸取了教训,我们带着矿灯,但是不打开,进入甘蔗林的动作也更轻了,等我们走到甘蔗林中间时,才突然打开矿灯。只见我们眼前,一只大雁嘶哑地叫着,拼命往旁边逃窜,但是,它的动作有些笨拙,有些无力,我们一下就抓住了它。
原来,这是一只受伤的大雁,下腹部有个大伤口,血肉模糊,或许是枪伤的吧。被我们抓住时,它还在不停地挣扎,挣掉了许多的灰色羽毛。
正在我们高兴的时候,旁边不远的甘蔗畦里,忽然传来一阵扑楞楞的响声,原来是附近的一只大雁扑腾着跑掉了。我们一时觉得有点可惜,要是能够抓到另外一只,就更好了。
一旁的堂弟说,这肯定是一对的,大雁都是一夫一妻的。这只受伤了,它就在附近陪着,要不然,它们晚上睡觉也有站岗放哨的,我们很难抓到。
抓到大雁,我看它受伤,先养下来。我找到一管用过的红霉素软膏,给它的伤口抹了一些,再用布条简单包扎,然后把它放在柴禾间里保暖,并且放了一些水和稻谷。为了防止它跑掉,我用绳子拴住了它的脚。
起初,大雁不吃不喝,眼神疲惫,蜷缩在我做的稻草窝里。过了两三天,伤口好些了,新肉也开始长出来了,它就渐渐地喝一些水,吃一些稻谷,有时还“嘎嘎”地叫两声,但是叫声不是很有力。
正在大雁一天天好起来时,那片甘蔗林却被砍伐收割了。农人们拿起短锄,把甘蔗一畦畦放倒,然后用弯刃的弧刀削去蔗根蔗叶,尾巴一砍,放在一堆,拿蔗叶卷成绳子,头尾各扎一条,一捆甘蔗就捆好了。捆好的甘蔗被农人搬到路边,用板车拉到糖厂修建的小火车路边,装上只有外框的火车,推到火车站,过磅,晚上再由糖厂的火车头拉到糖厂压榨。
收割好的甘蔗地在冬天的寒风中特别萧瑟。留着甘蔗头的一畦畦甘蔗畦,整齐地排列着,让这片原来风吹沙沙的温暖的甘蔗林,显得特别落寞。
甘蔗地上空的黄昏,每天依然有雁群飞过,它们有时会在那里盘旋一会儿,不时地发出一两声鸣叫,声音显得沙哑而悲苦,仿佛是在留恋它们曾经温暖的家。我不知道这里面是不是有那只受伤的大雁的伴侣,不知道甘蔗林砍掉之后,它们要到哪里过夜?
受伤的大雁已经恢复得差不多了,食量大了很多,每天都扑打着翅膀,想要飞走。它的伤口被新长出的皮肤覆盖,虽然无法长出羽毛,但是旁边的羽毛能够部分掩盖那个伤口,伤口位置也不那么突兀了。
我们决定把大雁放了。
黄昏,我和堂弟们抱着大雁来到甘蔗地。
夕阳依旧动情地在大地上点染着金色,好像从来不知疲倦。甘蔗林已经不在了,它就把颜料洒在甘蔗地上。
看到大雁鸣叫着飞过,就把那只大雁扔向天空。大雁挥动着翅膀,发出呼呼的风声,兴奋地向雁群飞去。
我希望飞过的这群大雁就是那群栖息在甘蔗林的大雁,我希望它能找到那只它受伤时陪在它旁边的伴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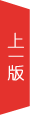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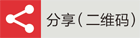
 前一期
前一期
 闽ICP备06035371号 闽公网安备35030002001038号
闽ICP备06035371号 闽公网安备35030002001038号